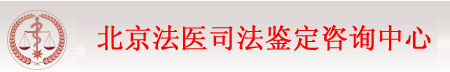原标题:范雨素消失半年后现身:日渐拮据,写完去做保洁员
【微纪录】消失的范雨素
编者按:
再翻几页,2017年的日历即将收起。中国变化太快,稍不留神,就会错过许多大事。
人所周知,文明不止是大江大河,还有生活在河岸上如同你我的普通人。
江汉平原上,年初去世的毛银梅老人是纪录片《二十二》的主角之一,临终前她依然没有与自己的“慰安妇”历史和解,却让更多人思考他者的命运。在北京皮村里写作的范雨素,成名并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大凉山火塘边,消失在格斗场的孤儿们,不知道未来的出路。还有上万名被卡在北京“3·17新政”中的买房人,一步之遥成了步步之遥,却并未弃守生活……
我们记录这些曾经的新闻人物,他们的断裂、迷茫、悲欣交集、惶惶不安,记录那些命运的转折处、情感的深处以及现实的背面——这些生命与表情共同构成了2017的一部分。
人事有代谢不假,往来成古今可鉴。

原标题:范雨素的五张面孔
文|孙俊彬 图|孙俊彬 编辑|王珊
名人范雨素
范雨素住的地方叫皮村4X号公寓,这里是前村委书记的家,她把这个两扇大红门的院子称为“下野总统的府邸”。
11月21日晚上,一个警察带着三名治安人员闯进了她的小屋。最近,全北京正在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活动。
“名人”的身份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特权。治安人员收走了一些有安全隐患的物品。
几天后,在皮村商业街旁边的一家快餐店里,范雨素用她惯常的平淡口吻说起这件事,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那有什么,穷人无非就是算钱的帐,高高兴兴让他拿。”她轻轻地甩着手说。
出名似乎并没有改变范雨素的生活,更没有像有人预测的那样完成一次“阶层跃升”。
今年4月,《我是范雨素》一文走红之后,皮村突然涌进了超过50家媒体和近30家出版社,一家出版社拎着20万元订金找范雨素签出版合同,最后连人影都没见着。重庆的一家媒体说她“压力过大躲入深山古庙里”。
“瞎扯!我一直待在家里没出门,电话关机,天黑了还是照样大摇大摆出去吃饭,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问及为什么躲开媒体,她半开玩笑地说,因为媒体把她拍得太丑了。
私底下,范雨素密切关注着网上对她的评价。一篇文章说她是因为中产阶级的悲悯才出名的,为此她伤心了很久。
5月,一家网络媒体带着诗人余秀华造访皮村。组织方希望范雨素能现身跟余秀华做一场对话,然而,直到余秀华离开,范雨素还是没有出现。
不久之后,余秀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炒作,肯定是炒作,说什么‘媒体采访太多了,为了躲避采访跑到山上去了’,我就不相信这种话。”
对于余秀华的质疑,范雨素显得愤愤不平,“凭什么说我炒作,我又不认识她,没什么好说的。”
对于成名,她保持清醒,甚至过于敏感。11月22日,在一个自媒体大会的受邀发言上,她用标志性的轻盈幽默感形容自己的出名,“我在今年4月偶遇了一场沙尘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
这是她消失在公众视野半年多以后,首次在大型公共活动里露面,她为此花了30块钱在皮村的照相馆拍了张半身肖像给组织方做海报。主办方给她化了妆,她看着照片,显得很满意,“像个韩国明星一样。”
不过,事后她又很后悔参加这次活动,“太穷了,要不是没钱,我才不愿意这样抛头露面,都是虚名浮利。”

(范雨素在演讲现场。)
和许多一夜爆红的人不同,范雨素没有把自己偶得的名声变现,她谢绝了商业活动,联系采访的记者被她一一拒绝,对家人的打扰更是她不可逾越的底线。
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张慧瑜理解范雨素的选择,“她不愿意被任何东西绑架,拒绝被标签化,只有这样,她才能更自由地生活和写作。”
4X号公寓南向一间8平米的小屋是范雨素的家,屋里堆了几千本书,她把这个屋子叫做“第欧根尼的狗窝”,10年来几乎没有客人造访过这里。南向有一扇玻璃窗,玻璃很厚,冬日的太阳照射到被单上,她每天懒洋洋地躺着,觉得这是最幸福的生活。
半年来,她在这里闭门构思和写作。这就是她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世外桃源怎么会有人敲门呢?”她说完笑得头往后仰。
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订了长篇小说的出版合同之后,范雨素辞退了育儿嫂的工作。但她说出版社还没支付定金。日子渐渐拮据。在上海工作的大女儿渺渺每天给她打电话,催她出去干活:“干体力活才能有饭吃,写东西能赚什么钱。”
小女儿枝枝嘲讽她说:“你啥名人,人家鹿晗、王俊凯才叫名人,你看你穷成啥样,好意思叫名人。”
《我是范雨素》之后,外界期待范雨素的新作能带来更大的惊喜,范家上下却有另一种共识。范母张先芝按照她“政治家”的敏感,担心有“文字狱”的灾害,劝她别再写文章。她通过当地媒体,委婉地告诉女儿,“名气不能当饭吃,当好月嫂带大娃子。”
范雨素对此表示同意,“我要把它删成10万字,交给出版社,然后就回去做保洁员,随便干个什么都比这个轻松。”

1/2富人,1/2穷人
11月25日,范雨素现身北京798一个家政工摄影展。她在一张家政女工照片前伫立了很久,“她脸上的表情跟我脸上的表情是一样的,那种抗累、低调感的家政工表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褪去“名人”的虚幻光环,范雨素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家政工。她在北京当了11年育儿嫂,每个月的收入6000多块钱,这份工作帮她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女儿。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职业像家政工一样能在物质生活的冰火切换之间体验到阶层间的生存落差。
一周7天,范雨素6天住在富人家里。她帮忙雇主照看孩子,给他们喂奶,住最好的房间,睡在几万块钱的床上,和雇主家一起吃美味的饭菜,屋内装饰豪华,室内温度一年四季保持26度。她跟过的最阔绰的雇主,家里有1000多平方米,12个卫生间。
“像我手脚这么不利索的人很适合做保姆,我讨厌每天想着钱,保姆不用每天想钱,熬时间就行。”对自己的工作,范雨素觉得很满意。
她对北京蓝色港湾国际商区的饭店和咖啡馆了如指掌,吃过东单君悦酒店500块钱一位的自助餐,跟雇主一家住过三亚湾的五星级酒店。有一次雇主给了她5只肥硕鲜活的阳澄湖大闸蟹,她不知道怎么吃,拿回家晾在屋外,最后螃蟹都奄奄一息了。
聊起这件事,范雨素继续用标志性的轻盈幽默感形容自己,“我是1/2富人,1/2穷人”,说完拍着桌子哈哈大笑。
文章《我是范雨素》写过她在雇主的如夫人家里工作的故事,雇主是个上了胡润富豪榜的企业家,家里有管家、家庭老师、武术老师、厨师、保安还有家政工。如夫人每天晚上精心打扮等待着“丈夫”回来。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企业家和他老婆一起的合影,看起来也很恩爱啊。”范雨素说完,又开始怜悯起那个如夫人。
只有在极少数的时候,她会有被刺痛的感觉。有一次跟雇主去亲戚家里吃饭,雇主的亲戚给她拿来了一双一次性筷子。

周日,回到北京东六环外的皮村,见到小屋子里的两个女儿,她才感到真正的快乐。
皮村因为位于航线正下方而无法拆迁盖高楼,大量外来人口得以栖居在此。鳞次栉比的厂房、商铺和廉价公寓占满村庄,郊区富人们常常拉着几条狗在街上逛,其中一户人家出门拉着12条狗,范雨素称它们为“狗军队”。
大女儿渺渺15岁生日时,范雨素带着女儿和她的朋友到皮村村口的德克士餐厅吃了一顿,花了90块钱。
不久之后,雇主的孩子过生日,他们在颐堤港酒店办了一场生日派对,邀请了幼儿园的所有小朋友,还雇了一个魔术团队现场表演。通常在这种时候,家政工范雨素就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一个“用低廉料子织成的隐身衣包裹的人。”
“所有人眼里都没有我,我看得见所有人。”在巨大落差的生存环境中来回切换,范雨素没有表现出任何哀伤或者愤怒,“我以旁观者的视角看人世间的繁华和苦难。”
很多人对《我是范雨素》一文的语言风格感到好奇。范雨素的发现者淡豹认为,“她好像一位局外人,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写人物的可笑可叹。”
也有人指责范雨素在文章里泄漏了雇主隐私,不懂得感恩。范雨素认为这是对她的误解。她觉得自己只是写出了一个普遍现象,不针对任何人。“我对人都怀着善意,从来不会说别人一句不好。”
北京顺义有位女雇主跟范雨素一样也是单身母亲,她们保持了7年的联系。女雇主看到了她的成名文章后,打来电话,“小范啊,你的文字还是中等水平,要继续努力啊。”

(范雨素参加活动时遇到了记者。)
紫丁香与蜀葵花
范雨素的文学启蒙跟她的小姐姐有很大关系。她的内心有一道高墙,对人性不信任。只有提到小姐姐的时候,她的眼睛才会突然发亮。
范雨素的家在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范家附近有座鹿门山,唐代诗人孟浩然在此耕作、写诗。如今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在1980年代的内地小村庄里,范家的5个孩子粗茶淡饭,却享有着丰富多元的精神滋养。
母亲按照女儿出生月份的花给她们取名,小姐姐叫范梅花,她叫范菊人。小姐姐像她父亲,长得俊秀飘逸,小时候有腿疾,行动不便;范雨素像母亲,长得不出众,性格刚强,半生漂泊。
范雨素和她的小姐姐,就像一块美玉,掰成两半,她们各得其一,在对方身上寻找残缺的部分。
哥哥为了考大学大量购书,童年范雨素和小姐姐经常脚对脚躺在床上看小说,小姐姐痴迷《红楼梦》,只要说出其中一句话,她就能告诉你是哪一章哪一节的句子。
在范雨素心中,小姐姐才是真正天才型的人物,比她强一百倍。小姐姐13岁就写了大量的诗歌,全班都在偷偷传抄,老师让她寄给《诗刊》发表,她不愿意,锁在抽屉里。
《我是范雨素》一文爆红后,小姐姐看到了文章,夸她写得好,她感到别扭,“她才是大神级的,该成名的是她,我啥都不是。”
少女范雨素通晓地理,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12岁那年,她从当年最流行的琼瑶言情小说《烟雨濛濛》书名中受到启发,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范雨素。她从知青文学里学会趴火车,偷红薯的伎俩,孤身一人逃票去海南游荡。在海南期间,她身为分文,靠吃水果、捡垃圾桶里的食物为生。
三个月后,范雨素回到家里,被村里人指责为离经叛道。只有她的小姐姐兴奋地询问她南方有海的世界。
范雨素少年时读蒙田、休谟、柏拉图和介绍第欧根尼的著作,但是她读不懂,小姐姐告诉她,“读不懂不是你笨,是翻译太差劲,你要做中国的第欧根尼。”
第欧根尼是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范雨素能背诵他的全部语录。她最想去的地方之一是科林斯,因为那是第欧根尼的故乡。
“从哲学中,我至少学会了要做好准备去迎接各种命运。”第欧根尼说。
范雨素小时候的绰号叫“懒曲蟮”(襄阳话,意为蚯蚓)。书里告诉她,这是一个物竞天择的世界,适者生存,她担心像她这样走路比蜗牛还慢的人以后会被淘汰,会饿死。
“我决定找哲学家问一问,但是上哪找哲学家呢?”。她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管理哲学家的应该是哲学系主任,中国最好的哲学系主任应该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1992年寒假,18岁的范雨素穿着薄呢大衣和方口布鞋坐了一天的火车来到寒冷的北京,见到了北大原哲学系主任陈战难,然而,她千里迢迢带着的疑问并没有说出口。“我看陈老师太忙,没和他告别,起身就走了。”
两年后,因为“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范雨素辞掉了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只身闯荡北京。
比她大3岁的小姐姐继续留在乡下做代课老师直到转正,丈夫嫌她整天写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她索性不再写了。
姐妹俩的命运在此分岔。范雨素把小姐姐比喻成诗意般的雨后紫丁香,觉得自己更像容易成活的蜀葵花。
母亲张先芝一直认为小女儿是个爱折腾的人,“待在家里,像她四姐一样当个老师多好。红菊(范雨素)心思重,还没参透活着是为了啥。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范雨素出走之后就很少再回家,和她的小姐姐11年没有见过面。“她过得比我幸福多了,不用像我这样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卑微地生活。”范雨素说。

“底层作家”
2015年,范雨素在电视上看到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刑的画面。这个画面给她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她想起跟萨达姆同岁的母亲。“萨达姆是一代枭雄,结局却死得这么悲惨,我母亲在村里的执政时间比他还长,现在还健康地活着,我觉得我母亲比他幸福。”
人的灵魂并没有因身份而不同,这个认知促使她开始构思动笔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一年,她辞掉了家政工的工作,改做保洁员小时工,从旧货市场买了一大叠草稿纸,没活干的时候就闭门在家写小说。
在小说里,打伙村是范雨素获取素材的经验空间,她怀着悲悯之心写她最熟悉的家族故事。

范雨素的家族类似一个当代社会阶层的大杂烩,堂哥在中央部委工作,小姑姑是湖北省委的官员,小姨妈曾经做汽车运输发财。然而,在她看来,因为身份差距,家族之间人情冷漠。
她说,“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停顿了一下,她又补充说,“或者叫科幻小说,叫什么都行吧,我又没上过学。”
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想,“为什么我的叔叔能‘力拔山兮’,他又没练过武功,难道生下来就是这样?”。于是,她买了4本量子力学的普及读物,整天研究量子理论,最后找到了解释根据:光子的波粒二象性。
“光子的波粒二象性的特性就是可复制、具有不确定性和平行空间。我叔叔为什么力拔山兮,因为他身上有项羽的力量。”她认为量子力学看起来挺高大上的,其实就跟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这个发现构成了她在写的“科幻小说”的理论来源。
范雨素在《正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农民大哥》就是从她在写的小说里摘出来的。
11月19日晚上的皮村文学小组聚会上,范雨素从冷风中拎着三个手臂宽的袋子走进“工友之家”的办公室,像展示富足的家当般骄傲地堆到桌子上,“这就是我的手稿,十几斤重,大概有100多万字,写死人了。”
新作的书名叫《复仇的奥特曼》。“我写的是我们家族的故事,用量子理论中的多重空间和光的波粒二象性,让项羽和李煜这些帝王将相在我写的人物身上复活。”范雨素翘起腿,用溅珠落盘般清脆急促的声音讲诉她的小说梗概,所有人听得目瞪口呆。
“其实很简单,他们的今生是草芥小民,但是前生很可能是帝王将相。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人不分三六九等,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她最后笑着说。
她文学里的理想世界既不是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世界,也不是充满自由市场的幻觉的当代资本世界,而是一个无阶级差异的乌托邦世界。
张慧瑜听完她的新作介绍之后也感到惊奇。在他看来,“范雨素的写作不在纯文学的范畴内,很难归类。她从动画片、儿童歌谣、多重空间等等这些经验和理论里抽取出来词语,然后拼贴在一起,语言有跳跃性,很少见。”
对于范雨素的新作,文学小组的成员胡小海说,“期待范姐的新作颠覆我们的想象,把这个千疮百孔两极分化的社会震得天翻地覆。”
《我是范雨素》爆红之后,媒体成功地塑造起一个为“底层的呐喊”的范雨素,范雨素拒绝这种代言,“我就是一个社会底层努力求生的弱者。”有媒体称她为“底层作家”,范雨素并不同意,“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18岁那年的北京之行,她的困惑没有得到回答,许多年后,她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个世界还是那样,每个人都充满了焦虑,恐惧。”

(皮村商业街上的范雨素。)
生长就是目的
范雨素不喜欢别人拿她跟萧红比。“萧红抛弃自己的孩子,她是懦弱的人,我比她强多了。”
出于对女儿的保护,在外人面前,范雨素刻意隐瞒单身母亲的身份,她总是告诉别人,丈夫是个“装修工”。
和母亲取名的随意不同,范雨素给大女儿取名范苗苗,小女儿叫范枝枝,来自唐诗“一树春风千万枝”。苗和枝就像一棵生长的小树,范雨素引用杜威的话告诉女儿,“生长就是目的。”
大女儿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太“萌萌哒”,和母亲年少时一样,14岁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范渺渺,她觉得渺这个名字既是浩渺无边,又是渺渺茫茫看不见。范雨素没有办法,只好随她去了。
范渺渺今年20岁,在上海一家文化公司当速记员,一个月工资1万多块。她的qq签名是“农民工二代,飘二代”。范雨素看到之后很伤感,觉得女儿的好职业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归属感,依然是惶恐的。
也是20岁的时候,范雨素只身来到北京,她在饭馆做了几个月的服务生,因为手脚不利索,好几次打碎了盘子,不久之后就辞职了。接着,她转行在路边摆摊做小买卖,就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后来的丈夫。
范雨素把这段婚姻的肇始解释为,“就像张爱玲说的,不早也不晚,正好碰上了。”
对于那个来自东北的前夫,范雨素对他的印象只剩下一个彪悍的背影,“从来不生病,冬天也只穿薄薄的大衣。”
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丈夫的生意越做越不好,两个人经常吵架,丈夫爱喝酒,喝醉了就动手打她。
结婚5年多之后,范雨素提出离婚,全家人都阻止她,只有小哥哥支持她。范雨素其实早已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婚姻。“摆脱了一个噩梦,饿死了也清静。”她说。
离婚之后,范雨素带着两个女儿疲惫不堪地回到湖北老家,然而,故乡没有给她喘息的机会。家里突然多了三张吃饭的嘴巴,大哥哥不太高兴,说了几句重话,没住几天,范雨素就带着女儿回到北京。
大女儿经常抱怨她不会经营婚姻,她觉得委屈,“我只是年轻的时候看人不准,遇到这么一个烂人。”
对于这段不幸的婚姻,范雨素认为跟她生的是女儿有关。她在一个养奶牛的家里看到小公牛因为性别被宰杀,她很难过,觉得女儿也是因为性别被父亲抛弃的。
于是,她找了好几个在国外留过学的人,问他们国外的小公牛是怎么活下去的。
女儿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然而,生存迫使她无法像大部分母亲一样陪伴和呵护孩子,为此她常常感到愧疚。当家政工的时候,有时雇主的孩子半夜醒来,她就要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他入睡。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想起她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她在文章里写道。
在皮村,范雨素没有朋友,婚姻的挫败和求生的劳苦使她对任何人都始终保持警惕,即使跟文学小组的成员也只是“点头之交”。她总是在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后,补充一句,“我不爱跟人说话,我是有自闭症的人。”
张慧瑜理解范雨素这种性格,“她和人的关系跟她单身母亲的身份有关,她没有其他依靠,只能靠自己保护孩子。”
因为户口问题,女儿没办法在北京上学,范雨素从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买了1000斤二手书,放假的时候就在家里给女儿读《小王子》、《苏菲的世界》、《儿童哲学》还有颜子的《箪食瓢饮》。
大女儿渺渺6岁就会做饭,母亲上班的时候,她在家里照顾妹妹。她记忆力超群,经常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文学经典段落,后来她成为一名速记跟她儿时的阅读经验有关。
小女儿枝枝在衡水一所中学念初一,考试总是考第一名。同学知道她家在北京,但不知道住在京郊六环外皮村的小屋里,这一点让她烦恼,她问母亲范雨素,“我们同学都住在大房子里,我们家怎么那么小?”
买个房子是母女三个人最大的愿望,可是在北京这个愿望的实现概率并不高。“我能力有限买不起,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没有让她们变成无妈的孩子。”范雨素说。
范渺渺无数次地承诺以后不会抛弃母亲,要给她养老。但范雨素自己心里做好了打算,“她结婚了,我死也不会跟着她。我想去云南或者海南找个地方一个人住着,我觉得这样就是幸福的。”
儿时的范雨素曾经得过一次急性肾炎,幸亏母亲及时带她治疗才捡了条命。村里有三个同龄的孩子,一个得了慢性肾炎死了,两个得了肝炎死了。许多年后,她依然觉得自己还活着就是上天的恩惠。
“活着就是活着的过程,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