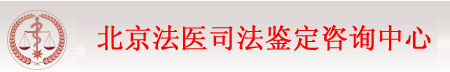原标题:台湾“寻三代”的大陆之旅:我们是两岸飞行的蝙蝠
文|王一然 编辑|王珊
(去年夏天,童桐带着父母到大陆开始寻亲之旅。路线从台北到广州,然后到长沙,再去南京、芜湖、杭州和上海。视频由受访者提供)
倚在长沙出租车的车窗上,母亲的皮肤有些泛黄,宽大的墨镜也没能遮住眼睛附近的抬头纹和黑褐色老年斑,车窗外商铺喧嚣,住宅林立,双层巴士与路边的人群一晃而过,“那时候我太小了,只记得他一回家就伢子、伢子的叫。”她微微抬头,讲起残存在记忆里的故乡。
“我们这伢子就是孩子。”出租车司机笑着插话。
母亲听后向车座后背靠去,“真是……叫什么,齿牙动摇,两鬓斑白,然后又回到了长沙。”
这是童桐拍摄的家庭纪录片中的一个片段。今年四十岁出头的她,在台湾一家报社工作,从小在台湾长大,可以讲一口标准的台语,只有提及家庭背景时,才会被发觉是“外省人”(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到台湾定居的大陆人)。
童桐的母亲出生在长沙,父亲出生在福州,外婆是安徽芜湖人,“外省人”是三代人共同的标签。
“我外婆一辈子不属于台湾,她对自己的身份很清楚。”在童桐的记忆中,外婆对台湾没有任何归属感,“他们是仓惶逃到台湾的,当时以为过几年就回去了,没想到一逃出来就是五六十年。”
童桐的外婆于二十年前去世,母亲如今也年逾七十。去年夏天,母亲受伤短期行动不便后,童桐突然发现,她那么老了,如果再不带她出去可能就没机会了。童桐放下工作,带父母开始寻亲之旅。
“我真是赶鸭子上架。”临出门时,母亲嘟囔着。与1990年代第一代外省人的寻亲潮不同,童桐的母亲很少提到大陆,不再对返乡有执念,大陆的轮廓早消逝在父辈零星的描述中。
“包括这次寻亲旅行,也是我拖她出门。因为我妈和我爸一辈子都在台湾奋斗,想要给我安稳的生活,他们没有回大陆的念头,也几乎不会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连养家糊口都来不及,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这些。”童桐说。
作为继续完成祖辈寻亲愿望的第三代,早在台湾读研究生时,童桐就写过论文,探讨外省三代的身份认同,她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外婆那一代人比较清楚自己是谁,他们一辈子也不属于台湾,每天都在想着回去,没有归属感;父母这一代一生都在台湾奋斗,他们已经渐渐融入了台湾人的圈子,但还是知道自己的根在大陆;但我还在寻找‘我是谁’,很多人都问我们有没有认同感,我在想你们说的认同是认同什么?我应该是谁?”
寻亲之旅进行到安徽芜湖时,正是七月盛夏,空气热皱,母亲不停扇着扇子坐在一家小饭馆里,一直咧着嘴笑,“终于来了。”停顿了一下,她对童桐说:“回去要告诉她(外婆),芜湖好棒。”
离开台湾前一晚,母亲对着外婆的遗像絮叨了很久:“我们要回你的老家了,替你看看上海和芜湖变成了什么样子,你要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1970年代在台北的一次喜宴上,外婆、爸爸、妈妈和童桐。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童桐口述:
“要不要过来尝一尝”
外婆过世时,我就决心以后带妈妈走一遍外婆走过的路,母亲是为了寻根,我更想纪念我外婆,把她残缺的那部分补全。
我们制定的旅行计划获得了一个机构举办的比赛大奖,有十万新台币的旅行基金。路线是从台北到广州,然后到长沙,再去南京、芜湖、杭州和上海——广州是外婆和妈妈当年上船的地方,长沙是外婆结婚生妈妈的地方, 芜湖是外婆老家,上海和南京是外婆生活过的地方,杭州是爷爷的老家。
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们这趟旅行,羡慕母亲年纪这么大还可以回大陆,和女儿一起远足。但我们这代人其实和外婆那代不同,对寻亲没有那么多感情和情绪,因为我们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于大陆只有想象。
父母到大陆后很喜欢和人聊天,什么都能和人家聊起来。他们在南京雨花台附近碰到一对老夫妻坐在公园野餐,我妈就赶紧跑过去问:“自己弄的?看起来很好吃耶。”人家说:“要不要过来尝一尝?”简直正中我妈的下怀,我妈赶紧说:“哎那个看起来很好吃,我就吃那个好了!”
外婆是安徽芜湖人。小时候我让外婆讲芜湖话,外婆说的是走音的国语,但还坚持说是芜湖话。后来我们到了芜湖,拼命骗出租车司机多讲芜湖话,才知道地道的芜湖话都听不懂。当年的大宅子也都拆掉了,外婆这边关于亲人的线索已经很少了。

(童桐的父母在芜湖的长江边合照,这里距离外婆的老家很近,但老房子已拆,外婆这边的亲戚也无从找起,他们把长江当做故乡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真正意义上寻到亲,是找到了爸爸这边的堂叔一家,他们在杭州。我在我们家以前宅子的巷口见到一口井,只剩下这一口井了,在高楼大厦之间。我觉得眼前好像过幻灯片一样,好像看到大院子里有水缸,水缸里养了莲花和金鱼;好像见到了从来没见过的家人们在你眼前走动,生活,来来往往。觉得想哭。
在台湾时我父亲根本都不知道还有堂叔这么一支亲戚,是在台湾的爷爷的兄弟托人联系到,通知我父母去认亲。堂叔一家住在杭州上城区老宅子的回迁地,胡雪岩故居旁边,当年的宅子比胡雪岩故居小一号,现在已经是楼房了。
在杭州第一次见面,堂叔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们的长相并不相似,但能莫名感觉到是一家人。你能感到是DNA在呼唤,我母亲也在一旁流泪。
我在杭州待了十天,杭州有个跳广场舞的地方就在南宋太庙的遗址,一群中老年人跟着音乐在七百多年前的太庙跳舞,我觉得太有范儿了!我家旁边的植物园每天都有人跳舞,而且舞步和音乐竟然和大陆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有的音乐都是一样的,我在上海听到台语歌,好像是陈小云(台湾闽南语女歌手)的歌,感觉很震惊。
我住在堂弟家,每天都去堂叔家吃饭。饭桌上居然有小时候我在台湾奶奶家里吃的同样的小菜,连菜色也相同,而且堂叔家里也保留着家族的吃饭习惯,比如用小汤匙直接从汤碗里舀汤喝,喜欢吃千张包肉、蛋饺,每天的晚饭都有一盆大闸蟹……他们一直在讲杭州怎样怎样,然后期待我讲台湾那边是怎样的。

(寻亲旅行的高铁上,童桐父母合影。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大陆没有的水果我不要吃”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感兴趣。小时候有一个同学,家里有二十几本大陆的摄影图集,每一本都很厚,里面是大陆各个省份的图文详解,我每一次到他们家都要翻来看,然后借走;有一个老师送给我爸一套书,大概叫《中国五千年历史图鉴》,我一整个暑假都在看。
小时候我一有机会就缠着外婆讲她在大陆的事情。外婆一开始很少开口,我猜测这可能和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有关,当时是谈大陆色变的,虽然对我们这些阶层的人影响还少一些,但外婆很少会主动提起大陆。
外婆算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生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外婆的父亲和弟弟都在上海,父亲做律师,弟弟做公务员。外婆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家里养了人力车夫,每天送她去上学,但很快战争和动荡让外婆结婚并开始逃难,在长沙生下我母亲,没多久后,亲生外公就去世了。
外婆开始独自带着母亲流亡,最后在1949年来到广州,想从广州到台湾去,但是没有门路。四岁的母亲在海边拿着钓竿玩耍时,遇到了几个国民党青年军,都是大学没毕业就参军的年轻人。母亲长相可爱,抱着献宝的心态,和他们聊天,拉着他们去找外婆。
青年军称呼外婆“章先生”,他们给外婆出主意,让她补一个国民党二等兵的名额,这样就能带着母亲去台湾找舅公公。外婆就这样获得了去台湾的船票,她用布条将母亲绑在身上,让母亲紧紧抓住,巨大的轮船放下来数十条绳梯,人们顺着绳梯往上爬。外婆爬的过程中,邻近有的人就掉到海里,没人管他们。外婆晕船特别严重,我妈妈以为外婆快要死掉了,拿一个装饼干的铁盒和人家讨稀饭给外婆吃。船上有的人生了重病,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就死掉了,然后尸体就直接被扔进海里。
我从小看外婆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是民国女学生那种打扮,外婆做了一段时间教师后,嫁给了同样到台湾的继外公,继外公在大陆也是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每天拎着鸟笼子,腰里揣着一把刀,无所事事。随身携带的财物花光后,他们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

(童桐的外婆年轻时。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童桐的继外公抱着她舅舅。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生活虽然磨掉了外婆的小姐气,但也保留了一些仪式感,比如外婆一定要用庞氏冷霜化妆品,要抽三五牌洋烟,绣花拖鞋一定要台北西门町的老上海定做,她穿了一辈子。台湾有那么多种类的水果,外婆就只吃大陆有的水果,从来都不会买,拿给她尝也会拒绝。
过年时外婆带我到外省人好友家里拜年,会拎着《花样年华》里张曼玉那种方形的皮包,旗袍外面套天鹅绒面的西装外套,带翡翠首饰,然后我们进门就喊“恭喜!恭喜!”外婆朋友家里的桌子上一定会有果盒,里面放的都是大陆的食品,糖莲子、玫瑰瓜子、南枣核桃糕等等,小时候以为全台湾过年都这样,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台湾人从来都不吃这些外省食品。
外婆不经常提起大陆,但还是能看出一些痕迹来的。比如她喜欢听台湾人都不听的老歌,尤其是《落花流水》,我感觉这首歌比较贴合他们这代人的命运,她们在打麻将的时候端出那种上海小姐的架子,大声讲家乡方言,外婆经常赢钱,后来人家打牌是消遣,她就靠赌钱来贴补家用。
外婆和她圈子里的人每天都打牌,抽烟抽得很凶,就像《色戒》里面那些打麻将的女人四五十年之后的样子,她们会给我一副麻将让我在麻将桌底下玩,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同龄的孩子,我就在这个“老人院”看着她们打牌长大的。那时候没人想要在台湾买房子,甚至家具都是竹制和藤编的,很便宜,因为在他们心里,觉得三五年就回大陆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四五十年过去了。
他们这些人一直到蒋介石去世才彻底死心,当时在台湾的人应该都会记得蒋公去世前一晚突如其来的大暴雨。他们这些“流亡”到台湾的人,突然意识到可能今生都回不去故乡了,外婆会更绝望一些,她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就算后来外公回大陆寻亲,外婆也没有回去过。她心里惦记的地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在看电视的时候偶尔和我提起她上学的地方。
我们家里最早回去寻亲的应该是奶奶,大概在90年代初期;我妈第一次应该是95年左右,是回大陆玩,因为外婆这一脉已经找不到什么大陆的亲人了;我爸爸是2000年左右我在北京读书他才第一次到大陆来看我。
外婆这一代在90年代之后有“返乡热”,很多人回到自己的故乡痛哭流涕,但因为亲人都已经去世,外婆一直没有回大陆。
外婆去世的前两年就开始昏迷,断断续续醒过来会发脾气问,为什么你们还不让我走?所以其实她走得很痛苦。

(寻亲旅行的高铁上,童桐的父母合影。)
夜行的蝙蝠
我25岁时才第一次来大陆,到北京念书,飞机降落的时候特别激动,虽然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的航程,但太远了,远到是我外婆一辈子没法回来的路。刚开始大家很客气叫我“台湾同胞”,老师也允许我用繁体字交作业,大家上厕所有时候会不关门,感觉有些不习惯。母亲来北京看我时,喜欢听京片子,连人家吵架都要停下来听很久。
我堂弟堂妹他们的母亲都是台湾本地人,身上完全看不到大陆的影子,他们讲的台语比台湾人还台湾人。但我们这个圈子的人,父母都是外省人的,会刻意找大陆食物来吃,然后还互相比较不同地方的食物味道。
曾经有一个台湾美食部落格讲大陆的红豆松糕,说青红蜜饯很好吃。我当时非常火大,因为那个是江浙地区的糕点,那个根本不叫青红蜜饯,要叫青红丝!他一看就是没有吃过。
我经常在脸书上和人家吵架,我的朋友们就会开玩笑劝我说:“你收敛一点啊,咱们是在人家的地盘呢!”
我就反驳说:“什么叫人家的地盘,好歹我也在这里待了四十年唉,我为什么没有发言权?”但其实我知道,我们这类“外省三代”就像是伊索寓言里的蝙蝠:飞禽和走兽开战时,蝙蝠到两边去说好话,后来大家讨厌蝙蝠,说它既有翅膀又有腿,哪边都不算,只能在黑夜里独自飞行。
我们是住在市民住宅的,零星散落分布在台湾本土人当中,其实我们很羡慕住在眷村的孩子,因为他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住在一起。
但其实眷村的人和我们都属于底层到中产阶级,都不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像蔡康永他们家这种,才算是有钱人,但他们的失落更大,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和想象都会更大,因为他们失去的是更多的。
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同学彼此的家里的背景不一样,但不会互相歧视;父母的朋友也有很多本地人,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有人开始把我们分类,让我们彼此攻击。这些政客要借着人们的伤痕来实现他们的利益。我读大学时,台北市长与高雄市长的竞选晚会上,一名竞选人喊出“中国猪滚出去!”我在想你到底在骂谁啊?你不是在骂自己吗?在陈水扁执政时,有一句著名的话:太平洋没有加盖子,你们不想留在台湾就滚出去!他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外省人。

( 杭州寻到的亲人,童桐的堂叔堂婶到台北,与童桐的父母在鼎泰丰吃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的专业是新闻,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外省第三代的身份认同,里面有很多真实案例:一个29岁的台湾外省姑娘刘小姐,因为在香港工作的原因,要经常在台湾人、外省人、中国人的身份中切换,每次香港朋友介绍她时,都会说,她是台湾人。刘小姐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从来都说不出口我是台湾人。”刘小姐的父亲从小不准她看台语节目,也不许她学台湾腔和台语说话,她觉得父亲是在给自己催眠,怕自己忘记身份。
而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彰化人的尹先生更加不能接受,一次做房产中介的母亲客户打来电话,他接过电话后,对方劈头问:“你是不是外省猪仔?”尹先生很生气回击:“先生,你为什么出口伤人?”对方执意问:“你到底是不是外省猪仔?是,我就不跟你买房子。”
一些找工作的年轻人也吃了“省籍”的亏,一位去报社应聘的嘉先生在最终面试时,已经敲定了未来要负责采访的方向,但临走时,老板多问了一句:“嘉先生,你的姓在台湾很少见喔?”他回答:“是啊,台湾没太有啦,我们家是外省人。”嘉先生因此丢掉了这份工作。
在一些台湾人心里,是有“外省人原罪”的,他们对很多大陆的事情都很敏感,我觉得这会造成一种身份错乱。我原来认为,能改变我们这代人的出路在教育,但是现在小孩读书得到的教育是中国史属于外国史,可是你在过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你在姓中国的姓氏;你在讲国语和写汉字,这样的教育更会导致大家的身份错乱感,我们到底是谁?

(1980年代在高雄的爷爷奶奶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和童桐。)
我来大陆寻亲,人们会称我是台胞。我到了北京很喜欢吃北京的美食,但我一回台湾也会马上就跑去吃卤肉饭和贡丸汤,我的身上融合了台湾本地的生活经验和家庭给我的来自大陆的影响,为什么要逼我们去认同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融合”呢?
就像我有一个福建的同学,他在北京和父母一起待到13岁,因为户籍的问题要回福建高考,他从小在北京长大,说的也是北京话,但是他要回他老家高考,也不会有人特地跑来问他,你觉得你是福建人还是北京人?你对哪边更认同一些?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期待我们回答认同的问题,是发问者本身将我们分类,看做特殊的人,这个出发点是有问题的。
我一直想要修族谱,真正认识自己的家族,我想,当我不用再回答想做哪边的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认同,就只做一个简单的中国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搜狐号后窗出品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刘盛钱 UN649